(文章发表于2005年)
无独有偶,在十九世纪中叶,我国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在其10岁时也曾以菊花为题作过:“晨餐秋更洁,不必羡胡麻。”的诗句。其母亲见后曾预言道:“汝将来或不患无文,但少福泽耳” 。
未及弱冠的刘知白所呤出的“独看梅花瘦,玉骨纯洁色”的诗句。这也许正昭示了他孤傲风霜,艰涩困顿的人生,也注定了他艰难曲折而探索而创造的人生。
抗战时期,日寇逼近凤阳,刘知白举家离乡,靠治印鬻画以谋生。期间流离失所,迁徙途中常遇盗匪及遭日军的轰炸,致使行李散失,多年蓄藏之画几荡然无存。抗战胜利后举家返乡,但时局动荡,其再度携眷离乡,再入广西,在全县中山街设“白云铁笔馆”,刻印卖画为生,后因生计难以维持又辗转至贵州贵阳定居,直至解放后刘知白加入贵阳市刊刻社。后又调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国画室工作。在此期间,虽然颠沛留离,居无定所,生活困顿,但刘知白一边维持生计,一边不辍笔墨,画画成了他身处困境时对生活、对未来的追求和寄托。困厄中仍画笔不辍,诗书不忘。
文革开始后,人生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到刘知白的身上,因家庭出身问题,刘知白被下放农村,绘画工作被迫停止,大量藏书和作品,在几次抄家中也损失殆尽。下放到贵州省龙里县洗马河区乡下后,租住在农民家中,随行的只有体弱多病的老伴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。命运似乎对刘知白太不公平了,然而,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;天降大任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也许这正是上苍为刘知白开启的一扇通往成功的、进入一个更高艺术境界的大门。命运的多舛,赐予了刘知白一个深入接触山川造化的机会。如此直接地贴近山川大河,刘知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,他很快从打击和沮丧中解脱出来,忘情地投入到了绿水青山的怀抱。刘知白对自然,对贵州山水的认识和感悟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,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几十年的探索和积累仿佛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口子,一泻千里;几十年的探索似乎找到了一个支点,艺术之神似乎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他前面的山巅,一种新的画风正在此间孕化产生。
在当时的条件下,没有纸,刘知白就用各种包装纸、帐本、烟盒等一切可用之纸来写生,用报纸练字临帖,没有笔就用猪鬃和野竹自制画笔,并折回柳条烧成炭笔,以为写生之用。还从桃林中采取桃胶制成胶水来调和墨色。两年间,得写生稿5000余纸。落实政策后,刘知白一家得以返回贵阳。
尽管历尽艰辛,有时还有各种“运动”的骚扰甚至打击,但刘知白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画的追求和探索。刘知白在得法守法的基础上,下苦功,每日必画,从不间断,画画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唯一。由于长期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作画,他没有象样的书斋或画室,但几十年的研习,刘知白练就了一手不受条件限制,席地能书、钉壁能画的功夫,作画时无论山水花鸟、大幅小帧,都犹如成竹在胸,往往一气呵成,仿佛没有构思,没有沉呤,但却章法层出,气象万千,毫无陈旧、雷同之感,且表现出无穷的变化和无限的生命力。
在刘知白几十年的作画实践中,他对自己的习画历程总结为“法、守、功、化”四个字。在其所著的《绘事杂谈》一文中,对此有较为详尽的阐述:
“法”者,即方法、传统,即前人所创立的绘画技法、技能。刘知白认为:“凡习画者,须知有法,我等习画始,若不知前人之法,则必是东涂西抹,勉加成图。要使习画者能得前人某家之法必须先识其基本功法,掌握其寂静之画法与画理,以兹奠定其基础而后力求能发挥自家心得,以至深造,而免误入歧途。法者,非一二人智慧所能及,乃前赴后继,煞费苦心,积其智慧之结晶也,余故云,方法为第一要义。”
“守”字,即认识和掌握一定的技法、技能后,要巩固和提高。“习画即得其法,万万不可随学随丢,不自珍惜。……能守前人之法,方能从中悟出自家之法。”
“功”字,即苦功、用功。“当已知在学书学画中能够分得清楚‘法’和‘守’的关系时,则必须肯下苦功夫,练真本领,从有法以求有进,并能深知坚守法则是最可造成之因素,由是不至踏入歧途,即当力追前哲,以前人诸法,化合应用,从而成为己有,运用自如。”
“化’字,即化百家为自家,化有法为无法。倘于以上所说,习者都能做到,即能知其法则,复愿在较长时间中踏实作基本功,然后才能谈到‘化’字的道理。能把各家画法化合为一者,如明朝大画家之一的唐寅(伯虎),系用南北派画法合为一体,其师法北派山水,以斧劈皴为主,唐寅的老师周臣(东屯)师法南派山水用披麻皴为主。唐寅之画能在以两家之法合为一体而自成一家之法者,即是他能在法字上、守字上用功所得。此外,再游历名山大川,广师造化,溶冶一炉,独出新意,乃成为一代之宗师,为后人所赞服。…… 石涛大师云:搜尽奇峰打草稿,此语足以发人深思。要知石涛之画为何能高于当时的四王及其它画家之主因,非拘于学习前代某画家之法而已,更重要的是因他能长时期地去与山为友,与水为朋,游历名山大川以豁其心胸,旷其视野。可谓胸中具有丘壑,着笔自然成章。此是时,亦是化,世人皆云:师造化,而终莫能得其要旨者何也?我谓法尚未得,功亦不深,化将焉出乎!”
“法、守、功、化”四个字,体现了刘知白艺术探索的几个阶段。特别是最后“化”字阶段更是他自己多年的体验和独到的见解。正是这个“化”字了得,它体现了刘知白“学时有他无我,画(化)时有我无他”的治学思想。也正是这个“化”字,才有了刘知白艺术创作上的大生死、大创造,奠定了刘知白在中国国画史上的大师地位。
明代大学士王阳明在游历贵州时,面对贵州的崇山峻岭发出了“天下之山聚于云贵”的感慨。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长征进入贵州时,尽管其出生在湖南韶山,又带领红军上过井冈山,可谓见山不怪。但当这位伟人见到贵州的大山时,仍禁不住惊叹不已,留下了咏叹贵州大山的诗词《十六字令·山》。
山,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,离天三尺三。
山,倒海翻江卷巨澜。奔腾急,万马战犹酣。
山,刺破青天锷未残。天欲堕,赖以拄其间。
这是一个革命家、诗人眼里贵州的山。这里,诗人写出了那种云在山间,山在天上,云海翻腾,乌蒙磅礴的景象。由此可见贵州山水之独特神韵。
而刘知白眼里的贵州山水却更加丰富,更加精致,更加富于变化和更加具有灵性。他经常行走、伫立在风雨、霜雪、雷电之中,他悉心观察和捕捉大自然瞬间的变幻和天机,他潜心研究着贵州山水的表现手法。
在这里,刘知白所习练的传统笔墨找到了依托的实体,他描绘的对象也由漂泊无定变为固定明确。洗马归来的刘知白, 胸中有了气象万千的大自然,手中有了数千纸的写生稿。他要做的就是在已得法、守法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新的技法来表现这些自然。
刘知白落实政策回到贵阳,开始了他在修法、得法、守法的基础上,下苦功、笨功研习、体悟、修练,以求大“化”的转变历程。1976年“四人帮”倒台,“文革”结束,刘知白的心境、心态愈加平和,创作欲望、热情愈加强烈。加之1977年的登黄山和1979年的游苍山、洱海、青城、峨眉、更开阔了他的胸襟和创作的视野。他在一种自在的,没有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的情势下,创作了一批新的、有贵州山河精神的山水。
此时的刘知白已经从各方面做好了冲顶的准备,进入了他艺术生涯中最有激情,最富创造力的阶段。一条通往艺术高峰的道路似乎已经展现在了他的脚下。
刘知白或许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标准,也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大美至美,他的画也不能用一种什么美所能概括,只能说是兼而有之、神形兼备。
刘知白在参透古人的基础上,大彻大悟,真正进入了“我自有我法”的境界——创立了前无古人的大写意泼墨表现手法,以此写贵州的山,画贵州的水,表现了贵州山水那种水天相连,云山雾海、气象万千的神韵。使贵州山水第一次如此传神、如此深透、如此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如果王阳明当年能看到这些画,也就不会大发感慨了。
称其为前无古人的大写意泼墨山水,是因为刘知白的大泼墨法,区别于前人的各个流派,是刘知白对各家各派进行认真研读和探究,在研读和习画中,和前人交流,和前人神往而自己又另辟蹊径,独树一帜,可谓自出机杼又与古人相通。刘知白的泼墨山水,大气磅礴而又轻盈竣秀;亦真亦幻却又生动具体,贵州山水独特的神韵和风姿尽在那不可言状之中。
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刘知白大泼墨山水能得黔山野逸荒率的神韵,是由“写生”进而“写神”、“写心”、“写性”才能达到的境界。
更难得的是,刘知白秉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,力求用一种新的思维、新的语言、新的手法来表现贵州那独特的山水景观。使传统和现代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,于传统中透出现代意识。他晚年的作品表现出的构图上的随意,景象上的朦胧,似乎更能让人联想到意象、意识、朦胧、抽象等一些概念。然而,细细品味其作品,却没有那种凌乱、无序、怪诞的感觉,有的只是贵州高原那种水天相连、云雾缭绕、气象万千的神韵。于厚重之中显轻盈,于朦胧之中见清新,混沌模糊而又具象生动,看似信手拈来,实则匠心独具。给人一种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得出,伸手就能触摸得到的真山真水的感觉。这正是刘知白参透中国传统精神、传统哲学思想后所达到一种至高境界的表现。这种表现上的写意性与审美品质上的率真自然美已浑化为一。可谓水有形,山有道,大象无形,大道至简,这也正是大写意泼墨山水笔法的独特、精深之处。
大写意泼墨山水,是刘知白由师古人师造化之后,加上其人生阅历,积郁深厚,喷薄而出。他的泼墨山水,绝非文人墨戏可比。又因其淡薄名利于画坛之外,沉浸墨海以山水为乐,所以笔墨间特有一股天真野帅之气,这也正是其它受社会所累者所不可企及的心态与境界。
刘知白也许不是什么社会名流,在当今画坛上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,然而在他八十九年的艺术生命中,其面对暄器而坚守孤寂,面对物欲横流而甘守清贫;其身处困境而不废精研传统,历经磨难而不辍笔墨之耕,及至晚年终有所悟、终有所成。刘知白的一生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墨士的傲然风骨和独立个性。
刘知白的作品,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,到了八十年代开始有人关注和研究他的创作和作品。这时,慕名而来的、上门求画的人多了,拜师求艺的人多了,各种展览会、研讨会、年会什么的都上门了,有要推介他的、有要包装他的,然而,刘知白却一如既往地写生、作画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仍寄情于山水,生活在自己的笔墨世界里。
他的孤寂,是其高洁品行、超然性情的必然选择;他的清贫,是其不趋炎附势,不随波逐流的必然结果,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,只求独善其身的最好注解。
刘知白的一生可以说是为艺术而生,为艺术而活,为艺术穷尽了毕生精力而无怨无悔的一生。虽然他已经走了,但他却没有留下遗憾,也没有留下期冀,只给人们留下了对中国山水画不懈的、永远的探寻和追求。
刘知白走了,犹如他的泼墨山水,幻化于青山,幻化于绿水。
一个孤寂的灵魂,一颗高洁的心灵,在青山绿水间徜徉,在高天白云中升华。
在当今喧嚣的画坛上,有一个人是孤寂的;在近代众多的画家中,有一个人是超群的。他坚守寂寞而求修身齐家,他历尽艰辛而求物我融合。终于,经过几十年“法、守、功、化”的探索、演化,他悟出了中国传统文化、精神里那种大象无形、大道至简的真谛,完成了从有法到无法,从有为到无为的嬗变、升华,有如凤凰之涅槃,前无古人地创立了大写意泼墨山水画。为贵州的山水立传,为贵州的山水传神,成为黔山泼墨第一人。
人世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,转眼间已是知白先生诞辰九十周年。岁月流逝,而对他的崇敬和怀念,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淡远,反而一如秋日的红叶,越发鲜活、热烈。多少尘封往事,多少艰辛跋涉,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。
凤阳少年 小荷初露
刘知白出生在民国初年那个动荡的时期,成长于“五四”运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应该说,那个时代的刘知白可以有很多选择,象当时很多人那样,学理工以科学救国、学经商以实业兴国、考军校以杀敌报国,最不济也可以秉承家业,过着比较殷实、滋润的生活。而刘知白却偏偏对国学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表现出了超常的悟性,在上小学时的一次课考中,未及弱冠的刘知白就咏出了“独看梅花瘦,玉骨纯洁色”的诗句,受到了老师的赞赏。无独有偶,在十九世纪中叶,我国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在其10岁时也曾以菊花为题作过:“晨餐秋更洁,不必羡胡麻。”的诗句。其母亲见后曾预言道:“汝将来或不患无文,但少福泽耳” 。
未及弱冠的刘知白所呤出的“独看梅花瘦,玉骨纯洁色”的诗句。这也许正昭示了他孤傲风霜,艰涩困顿的人生,也注定了他艰难曲折而探索而创造的人生。
命运多揣 未夺其志
刘知白少年时期,正是“五四”运动风起云涌,迅速蔓延,对中国社会、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时期。受到新文化、新文学的影响,具有一定新思维、新思想的刘知白没有遵从父亲的愿望子承父业,去管理家中的财产,经营父亲的店铺,而是考入了苏州美专国画系,开始了他作为一个画人艰涩寂寞而创造而丰富的色彩人生。抗战时期,日寇逼近凤阳,刘知白举家离乡,靠治印鬻画以谋生。期间流离失所,迁徙途中常遇盗匪及遭日军的轰炸,致使行李散失,多年蓄藏之画几荡然无存。抗战胜利后举家返乡,但时局动荡,其再度携眷离乡,再入广西,在全县中山街设“白云铁笔馆”,刻印卖画为生,后因生计难以维持又辗转至贵州贵阳定居,直至解放后刘知白加入贵阳市刊刻社。后又调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国画室工作。在此期间,虽然颠沛留离,居无定所,生活困顿,但刘知白一边维持生计,一边不辍笔墨,画画成了他身处困境时对生活、对未来的追求和寄托。困厄中仍画笔不辍,诗书不忘。
文革开始后,人生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到刘知白的身上,因家庭出身问题,刘知白被下放农村,绘画工作被迫停止,大量藏书和作品,在几次抄家中也损失殆尽。下放到贵州省龙里县洗马河区乡下后,租住在农民家中,随行的只有体弱多病的老伴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。命运似乎对刘知白太不公平了,然而,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;天降大任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也许这正是上苍为刘知白开启的一扇通往成功的、进入一个更高艺术境界的大门。命运的多舛,赐予了刘知白一个深入接触山川造化的机会。如此直接地贴近山川大河,刘知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,他很快从打击和沮丧中解脱出来,忘情地投入到了绿水青山的怀抱。刘知白对自然,对贵州山水的认识和感悟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,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几十年的探索和积累仿佛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口子,一泻千里;几十年的探索似乎找到了一个支点,艺术之神似乎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他前面的山巅,一种新的画风正在此间孕化产生。
在当时的条件下,没有纸,刘知白就用各种包装纸、帐本、烟盒等一切可用之纸来写生,用报纸练字临帖,没有笔就用猪鬃和野竹自制画笔,并折回柳条烧成炭笔,以为写生之用。还从桃林中采取桃胶制成胶水来调和墨色。两年间,得写生稿5000余纸。落实政策后,刘知白一家得以返回贵阳。
尽管历尽艰辛,有时还有各种“运动”的骚扰甚至打击,但刘知白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画的追求和探索。刘知白在得法守法的基础上,下苦功,每日必画,从不间断,画画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唯一。由于长期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作画,他没有象样的书斋或画室,但几十年的研习,刘知白练就了一手不受条件限制,席地能书、钉壁能画的功夫,作画时无论山水花鸟、大幅小帧,都犹如成竹在胸,往往一气呵成,仿佛没有构思,没有沉呤,但却章法层出,气象万千,毫无陈旧、雷同之感,且表现出无穷的变化和无限的生命力。
艺途漫漫 上下求索
在美专期间,除学习各种专业课程外,刘知白还曾入朱竹云、张星阶先生创办的“百花画馆”研习国画,又深得国画系主任顾彦平(顾鹤逸之侄)先生提掖,收为私淑弟子。并于1935年住进顾先生设在怡园的“春荫书屋”,研习“四王及”吴门“画法,这期间,常随顾先生拜见苏州画界名流,因而有幸读到许多历代名家书画巨迹,得到名家指点,在此期间,刘知白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便,每每得到恩师及名家指点,加之耳濡目染,勤学苦练,画艺日长,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,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国画基础。在刘知白几十年的作画实践中,他对自己的习画历程总结为“法、守、功、化”四个字。在其所著的《绘事杂谈》一文中,对此有较为详尽的阐述:
“法”者,即方法、传统,即前人所创立的绘画技法、技能。刘知白认为:“凡习画者,须知有法,我等习画始,若不知前人之法,则必是东涂西抹,勉加成图。要使习画者能得前人某家之法必须先识其基本功法,掌握其寂静之画法与画理,以兹奠定其基础而后力求能发挥自家心得,以至深造,而免误入歧途。法者,非一二人智慧所能及,乃前赴后继,煞费苦心,积其智慧之结晶也,余故云,方法为第一要义。”
“守”字,即认识和掌握一定的技法、技能后,要巩固和提高。“习画即得其法,万万不可随学随丢,不自珍惜。……能守前人之法,方能从中悟出自家之法。”
“功”字,即苦功、用功。“当已知在学书学画中能够分得清楚‘法’和‘守’的关系时,则必须肯下苦功夫,练真本领,从有法以求有进,并能深知坚守法则是最可造成之因素,由是不至踏入歧途,即当力追前哲,以前人诸法,化合应用,从而成为己有,运用自如。”
“化’字,即化百家为自家,化有法为无法。倘于以上所说,习者都能做到,即能知其法则,复愿在较长时间中踏实作基本功,然后才能谈到‘化’字的道理。能把各家画法化合为一者,如明朝大画家之一的唐寅(伯虎),系用南北派画法合为一体,其师法北派山水,以斧劈皴为主,唐寅的老师周臣(东屯)师法南派山水用披麻皴为主。唐寅之画能在以两家之法合为一体而自成一家之法者,即是他能在法字上、守字上用功所得。此外,再游历名山大川,广师造化,溶冶一炉,独出新意,乃成为一代之宗师,为后人所赞服。…… 石涛大师云:搜尽奇峰打草稿,此语足以发人深思。要知石涛之画为何能高于当时的四王及其它画家之主因,非拘于学习前代某画家之法而已,更重要的是因他能长时期地去与山为友,与水为朋,游历名山大川以豁其心胸,旷其视野。可谓胸中具有丘壑,着笔自然成章。此是时,亦是化,世人皆云:师造化,而终莫能得其要旨者何也?我谓法尚未得,功亦不深,化将焉出乎!”
“法、守、功、化”四个字,体现了刘知白艺术探索的几个阶段。特别是最后“化”字阶段更是他自己多年的体验和独到的见解。正是这个“化”字了得,它体现了刘知白“学时有他无我,画(化)时有我无他”的治学思想。也正是这个“化”字,才有了刘知白艺术创作上的大生死、大创造,奠定了刘知白在中国国画史上的大师地位。
意气澎湃 敢凌绝顶
贵州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,其山形之奇特,山势之嵯峨,为贵州所独有。且贵州地处西北利亚寒流南下,印度洋暖流北上,冷暖流交汇的锋面之下,湿润多雨,气候多变。这就形成了贵州“地无三尺平,天无三日晴”的地理气候特征。山野浸润在水气雾气之中,灵秀而润泽,。山雨欲来时,但见远山白如洗而近山黑若墨。雨过天晴后,山青青而木秀,水盈盈而婉约。明代大学士王阳明在游历贵州时,面对贵州的崇山峻岭发出了“天下之山聚于云贵”的感慨。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长征进入贵州时,尽管其出生在湖南韶山,又带领红军上过井冈山,可谓见山不怪。但当这位伟人见到贵州的大山时,仍禁不住惊叹不已,留下了咏叹贵州大山的诗词《十六字令·山》。
山,快马加鞭未下鞍。惊回首,离天三尺三。
山,倒海翻江卷巨澜。奔腾急,万马战犹酣。
山,刺破青天锷未残。天欲堕,赖以拄其间。
这是一个革命家、诗人眼里贵州的山。这里,诗人写出了那种云在山间,山在天上,云海翻腾,乌蒙磅礴的景象。由此可见贵州山水之独特神韵。
而刘知白眼里的贵州山水却更加丰富,更加精致,更加富于变化和更加具有灵性。他经常行走、伫立在风雨、霜雪、雷电之中,他悉心观察和捕捉大自然瞬间的变幻和天机,他潜心研究着贵州山水的表现手法。
在这里,刘知白所习练的传统笔墨找到了依托的实体,他描绘的对象也由漂泊无定变为固定明确。洗马归来的刘知白, 胸中有了气象万千的大自然,手中有了数千纸的写生稿。他要做的就是在已得法、守法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新的技法来表现这些自然。
刘知白落实政策回到贵阳,开始了他在修法、得法、守法的基础上,下苦功、笨功研习、体悟、修练,以求大“化”的转变历程。1976年“四人帮”倒台,“文革”结束,刘知白的心境、心态愈加平和,创作欲望、热情愈加强烈。加之1977年的登黄山和1979年的游苍山、洱海、青城、峨眉、更开阔了他的胸襟和创作的视野。他在一种自在的,没有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的情势下,创作了一批新的、有贵州山河精神的山水。
此时的刘知白已经从各方面做好了冲顶的准备,进入了他艺术生涯中最有激情,最富创造力的阶段。一条通往艺术高峰的道路似乎已经展现在了他的脚下。
前无古人 黔山泼墨
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美学价值上,当代画家吴冠南认为,中国书画艺术有四种至美是值得画家穷毕生精力去追求的至高境界。一种是浑金璞玉,不雕不琢之形状,如万岁古藤,千年顽石。一种是雍容华贵,安详平和之美,如大漠孤烟,无波大泽。再一种是放浪不羁,野逸洒脱之美,如信马由缰,风卷残云。又一种是闲云野鹤,冷寂无声之美,如涧边幽草,水底栖鱼。刘知白或许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标准,也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大美至美,他的画也不能用一种什么美所能概括,只能说是兼而有之、神形兼备。
刘知白在参透古人的基础上,大彻大悟,真正进入了“我自有我法”的境界——创立了前无古人的大写意泼墨表现手法,以此写贵州的山,画贵州的水,表现了贵州山水那种水天相连,云山雾海、气象万千的神韵。使贵州山水第一次如此传神、如此深透、如此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如果王阳明当年能看到这些画,也就不会大发感慨了。
称其为前无古人的大写意泼墨山水,是因为刘知白的大泼墨法,区别于前人的各个流派,是刘知白对各家各派进行认真研读和探究,在研读和习画中,和前人交流,和前人神往而自己又另辟蹊径,独树一帜,可谓自出机杼又与古人相通。刘知白的泼墨山水,大气磅礴而又轻盈竣秀;亦真亦幻却又生动具体,贵州山水独特的神韵和风姿尽在那不可言状之中。
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刘知白大泼墨山水能得黔山野逸荒率的神韵,是由“写生”进而“写神”、“写心”、“写性”才能达到的境界。
更难得的是,刘知白秉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,力求用一种新的思维、新的语言、新的手法来表现贵州那独特的山水景观。使传统和现代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,于传统中透出现代意识。他晚年的作品表现出的构图上的随意,景象上的朦胧,似乎更能让人联想到意象、意识、朦胧、抽象等一些概念。然而,细细品味其作品,却没有那种凌乱、无序、怪诞的感觉,有的只是贵州高原那种水天相连、云雾缭绕、气象万千的神韵。于厚重之中显轻盈,于朦胧之中见清新,混沌模糊而又具象生动,看似信手拈来,实则匠心独具。给人一种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得出,伸手就能触摸得到的真山真水的感觉。这正是刘知白参透中国传统精神、传统哲学思想后所达到一种至高境界的表现。这种表现上的写意性与审美品质上的率真自然美已浑化为一。可谓水有形,山有道,大象无形,大道至简,这也正是大写意泼墨山水笔法的独特、精深之处。
大写意泼墨山水,是刘知白由师古人师造化之后,加上其人生阅历,积郁深厚,喷薄而出。他的泼墨山水,绝非文人墨戏可比。又因其淡薄名利于画坛之外,沉浸墨海以山水为乐,所以笔墨间特有一股天真野帅之气,这也正是其它受社会所累者所不可企及的心态与境界。
黔灵正气 山水清音
在中国历史上,凡成大器者,无不是那些信念坚定,独立特行,耐守寂寞,身处逆境却不失其志之人,屈原愤而赋《离骚》,司马迁羁而著《史记》,也有归隐山水自得其乐,留下佳话的陶渊明;更有隐世多年不为人知,直至后贤哲人发现,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才得以展现并彪炳史册的人物,一如中国画史上的大师陈子庄、黄秋园,又如刘知白。刘知白也许不是什么社会名流,在当今画坛上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,然而在他八十九年的艺术生命中,其面对暄器而坚守孤寂,面对物欲横流而甘守清贫;其身处困境而不废精研传统,历经磨难而不辍笔墨之耕,及至晚年终有所悟、终有所成。刘知白的一生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墨士的傲然风骨和独立个性。
刘知白的作品,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,到了八十年代开始有人关注和研究他的创作和作品。这时,慕名而来的、上门求画的人多了,拜师求艺的人多了,各种展览会、研讨会、年会什么的都上门了,有要推介他的、有要包装他的,然而,刘知白却一如既往地写生、作画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仍寄情于山水,生活在自己的笔墨世界里。
他的孤寂,是其高洁品行、超然性情的必然选择;他的清贫,是其不趋炎附势,不随波逐流的必然结果,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,只求独善其身的最好注解。
刘知白的一生可以说是为艺术而生,为艺术而活,为艺术穷尽了毕生精力而无怨无悔的一生。虽然他已经走了,但他却没有留下遗憾,也没有留下期冀,只给人们留下了对中国山水画不懈的、永远的探寻和追求。
刘知白走了,犹如他的泼墨山水,幻化于青山,幻化于绿水。
一个孤寂的灵魂,一颗高洁的心灵,在青山绿水间徜徉,在高天白云中升华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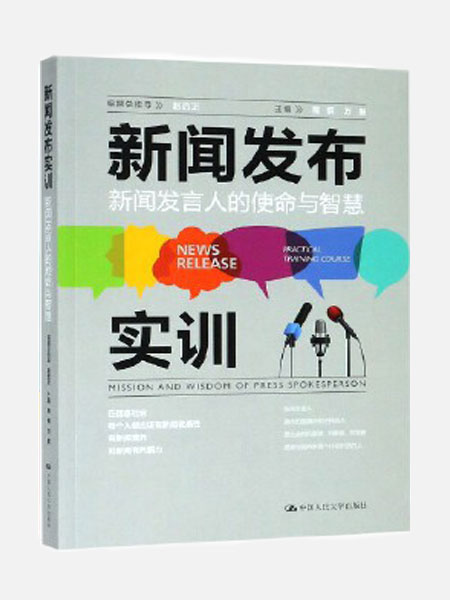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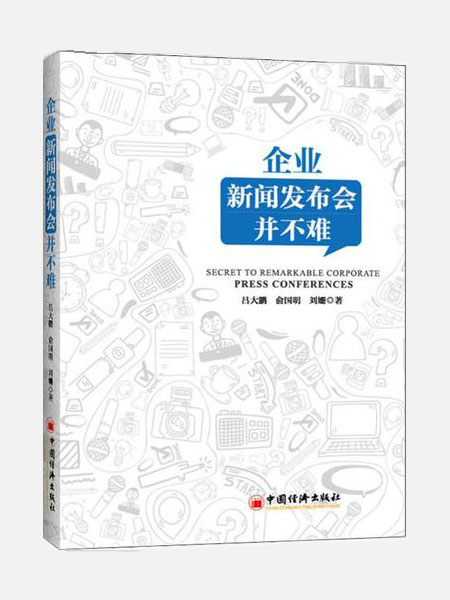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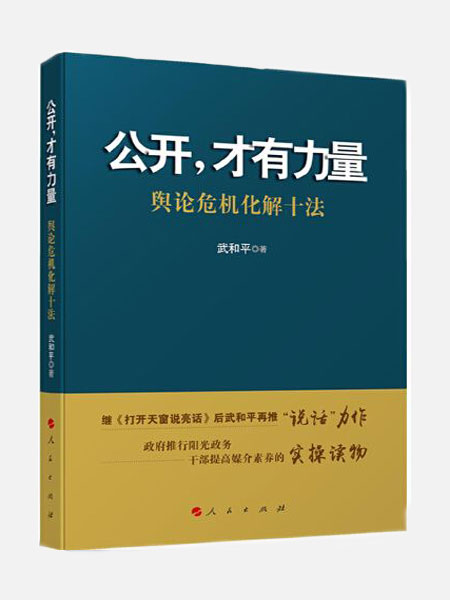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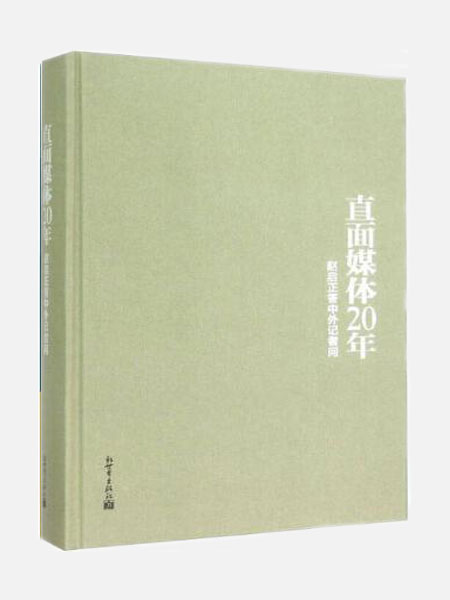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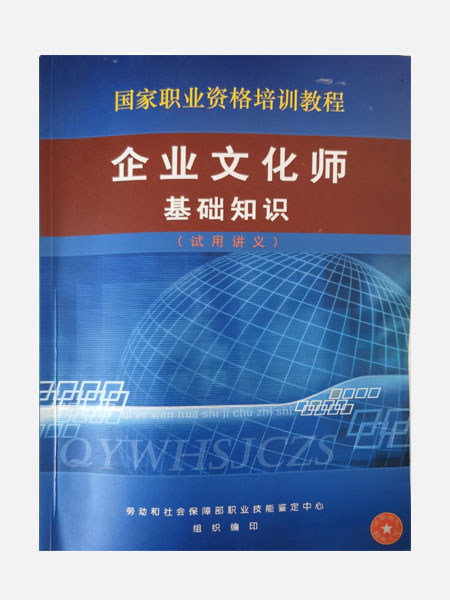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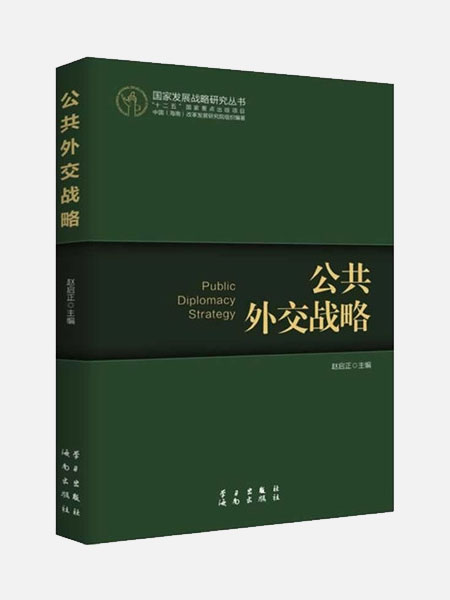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10118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10118号